中国琴学研究 | 论古琴音乐中的情感形象生理记录法(上)
论古琴音乐中的情感形象
生理记录法(上)
吴文光
历来的美学家和音乐学家从未间断过对音乐的内容和反映这些内容的途径、方法这一问题的研究、阐述和探讨,著作浩如瀚海,博大精深,确可从中获得教益和启发。虽然如此,我们却仍有必要对此再作一番细致的考察与进一步的研讨。
从音乐的内容上来讲,我想无非是以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作为反映对象吧。具体说来,所谓客观世界就是自然和人类社会,而主观世界则是音乐创作者和演奏者本身。至于音乐的形式和形式美,可以说是体现了审美主体对自然的认识,乐音本身可以划归为自然现象。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算作音乐的一种内容,但往往这种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某些规律性认识的“内容”被用来作为表现人类社会和人的艺术手段及形式。

这先姑且不论,让我们还是来讨论作为音乐内容反映对象的客、主二体之间的关系及音乐对它们的反映途径这一问题。鉴于音乐主要是听觉艺术的特点,音乐与其它视觉艺术的区别在于:视觉艺术可以通过复述表象而直接描写客体,而音乐对某些声音虽可模拟,但在这方面可为不多,而声音本身在再现自然物方面及人类社会方面也能力有限。因此,音乐大多通过表现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及受到客体作用的情感来较间接地反映客体。这点,大部分人疑义似乎不多。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家也早就指出了这个道理,例如:汉代成书的著名音乐理论著作《乐记》中就有“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的说法。这里首先提出了“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的观点,作者在这里不强调或基本否定了音乐在自然界有更多的直接对象的观点,而指出了主体和音乐的产生及内容有直接关联和重要作用。尽管如此,更为关键的是紧接着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这句话,它说明了客体的作用是第一性的,即客体作用于主体,主体通过声音来表达对客体的感受。应该认为这个观点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既强调了客观世界是第一性的,而且在此基础,上着重注意了音乐的特性。但音乐又是怎样来表现它的客、主两方面的内容的呢?换句话说,也就是音乐表现内容的方法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就是塑造音乐形象。
关于音乐用它特有的方式通过状声、模拟、比拟、象征等手法来塑造音乐形象表现客体和主体,前人之述可谓备矣。所谓的音乐形象它是一种听觉的形象,众所周知,听觉形象的概念性是不强的,它需要听者作广泛的知识性学习和符合逻辑的联想才能获得与创作意图相接近的一些概念。在音乐形象所包含的物态形象、事态形象(此为反映客体的形象)及情感形象(此为反映主体的形象)中,情感形象尤为重要,因为它是音乐最擅于表现的。在此,有必要来对我们所说的情感形象作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音乐之形象(基本上而非绝对)是抽象的、非再现的,它是基于人类对乐音这种自然现象的规律之认识基础上的一种艺术创造的成果。人类对乐音世界的认识和塑造音乐形象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状况,当然情感形象亦然。然而,当进一步去探讨音乐塑造情感形象的原则时,我们大体可以发现两种情况:
一是以典型的乐音结构和典型的乐音运动去比拟典型的情感心理概念。这是音乐发展和乐汇积累的一种结果,它是以西洋古典派以来的音乐(尤其是纯器乐)为代表的。它善于以一个情感的心理概念为主来进行多侧面的、立体的音乐造型。这种以声达意的作法确是造成了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音乐种类和作品、理论以及实践。
一是以乐音的运动和运动的乐音去记录情感的生理状态——它的变化过程。这是早期音乐塑造情感形象的突出特点之一。譬如歌唱,就是以曲调来记录主体情感的生理状态的例证。一首歌词的含义往往甚为广泛,有时多至数段歌词,但曲调只是一个,故曲调难于在以声求意方面充分发挥,它只是创作者受歌词感动后在情感的生理状态方面用乐音所作的一种直接记录。这正是以意求声的作法。这种作法同样也体现了音乐情感形象的抽象性,因为主体情感的生理状态大致可以用强弱、迟速、升降、规则、变异……及其它们之间的诸种复合变化等概念来表示,但这些概念并不等于情感的心理概念,诸如喜、怒、哀、乐等。所以,听者可以从前者来求索后者而不能直接具体感知后者。我们必须分清情绪和情感这二个常用词的区别,前者通常是指上述的情感的生理状态,而后者则往往代表了上述的情感的心理概念。情感和情绪之间,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生理反映。譬如“因悲哀而情绪低沉”,“因高兴而情绪激动”……。不难看到,一个情感的心理概念包含有多种情感的生理概念。另外,人类情感的变化是不规则的和有先后时间概念的,所以作为情感的生理反映更是如此。所谓百感交集只能是指在一段时间内所体现的一个情感变化的复杂过程,但在时间线上任何一点都是有先后之分的,所以音乐的对情感的生理直录上很少看到同时的多侧面、立体声现象,如有和声或复调现象也是由于心理、生理变化的强弱要求和进行多主体的情感生理直录。

现在,我们必须来探讨情感形象的典型塑造和直接记录塑造二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前述,一般地说直录塑造情感形象的方法之产生早于典型塑造情感形象的方法。在人类早期的音乐创作活动中,前者之用途最为广泛。我相信无论哪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普遍地采用过这种音乐创作方法,只不过由于自然环境、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不同而造成了不同的记录方式,犹如不同的语言文字对思想的表述和记录一样。而典型情感形象的音乐造型方法则是在初步总结直录法的基础上使乐汇典型化的产物(早期音乐的像声、模拟在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二者互相渗透、融合而不是绝对分割,只是在后期,西方随着乐器领城的革命而有可能在以声达意方面有所作为的时候,这两种方法的使用侧重面才明显地呈现出来。
那么,继续以采用直录法为主的中国音乐是否就落后了呢?笔者以为不一定。其理由一是中国的社会对体现这类方法的作品仍很需要;二是明代中叶后,特别是清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音乐家们把兴趣集中到对于情感形象直录法的研究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在古琴音乐、戏曲音乐及其它音乐上广泛而细致地研究了腔韵的形态及运用,使曲调的表现力向装饰音、滑音、嗽音、颇指、吟猱、各种复杂板式及节奏重音的不规则化、时间线上节奏任意切割的合理化、音色的多样性趣味、阴阳、强弱、刚柔、虛实……方面追求,单是古琴的吟、猱、绰、注就有数十种之多。这样,音乐在直录情感生理状态方面的表现力基本达到完善的境地,心有微动则无不可应诸弦上矣!

中国音乐在这方面的发展过程中时有产生强烈的追求心、声间的微妙吻合而使情感形象的典型造型或乃至旋律的作用降至次要地位的二者分离的趋向。戏曲音乐中的板腔或古琴音乐中的打谱正是这种趋向的体现。
古琴音乐中的打谱工作要求打谱者在对古曲进行打谱时注重调整客、我间的关系(此时古谱为客,打谱发掘者为我),即籍古谱之音以激发己之情思,从而使己之情思的来由有所渊源,不为无本之木,是方可合于古而发自己。若夫于古之谱一音未按而波澜已浚发于灵台,是必陷于盲目,既不能得古意,亦难于达己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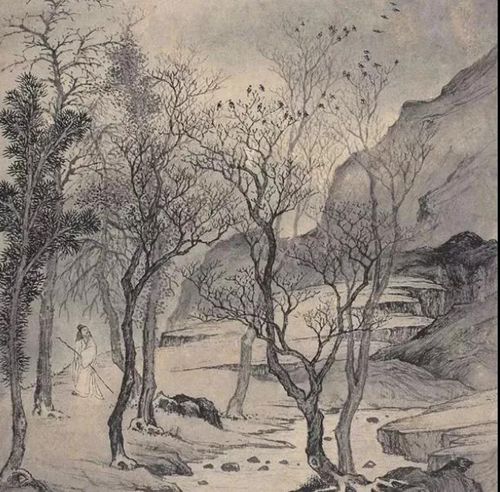
打谱与传派尚且存在的古曲演奏不同,有传派的乐曲主要是要求奏者的心理、生理状态去适应传统。当然,随着奏者艺术视野的扩大和艺术修养的提高,反转来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和提高也是必然的。而打谱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古代的乐曲由于传统中断,使原始作者和早期奏者在音乐形象的典型塑造及主体情感生理直录两方面的大部分意图处于隐性或不明确的地位。在音乐形象的典型塑造方面,由于古谱大多不记节奏,这种做法有可能使后代的琴家去进行在原有基础.上的最大再创造。而在情感的生理描写方面,后来的琴家除了对在谱式中有所标记的(如一些吟、猱、绰、注)进行窥视和探求外,这时有较大可能来阐述自已对古谱中的音乐的认识并通过实际演奏把它记录和反映出来。大部分琴曲在成曲后,通过审美主体的不断更替而得到了发展和丰富。中国音乐是注重自身更新的,这体现了中国音乐家重视对同一客体的审美认识的多面性和延续、继承性,它不偏重于以塑造客体的新的音乐形象的创造,而是强调个别的情感生理直录与有限形象塑造相结合的再创造。很明显的是,他们相信《乐记》中所说的这样一个原理,即:客体作用于主体,而音乐则主要是应该去表现那个受客体作用了的主体。
关于戏曲,在板腔和牌子音乐中也是和琴乐的情况基本相像,不过它在对于音乐形象的典型塑造方面更无须下太多的笔墨,因为可以借用唱词给人以语言、文学的生动形象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而演员的任务更集中于把词句对自己所产生的强烈感染所引起的情感上的生理变化通过声调、咬字、行腔等手段,把它们直接记录、表述出来。在这里,基本曲调的作用相当微弱,它只起到记录演员情感的音乐形象的乐音支柱的作用。演员可以节省在组合乐音结构方面所需花费的大量时间,这在演员一身须兼做、念、唱、打、编腔等繁重艺术劳动而缺乏强大的专业创作队伍配合的过去的中国社会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下面来谈谈这种以对审美主体情感的生理直录为主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哲学基础、社会历史背景和达到社会功效的途径。
总观中国哲学史上对音乐产生巨大影响的儒家和道家(佛教的影响在音乐上不明显),它们的音乐观可以概括为“中和之音”和“大音希声”两个四字句。“中和之音”强调音乐对人心的反作用,音乐既为心声,当其心欲过分时,应以适当的音乐去调整它。此为“逆欲法”。其间,司马迁肯定了屈原之怨,他在评价《离骚》时指出:“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肯定了屈原之怨的产生与抒发是自然的、合理的。司马迁进而认为,古来一切不朽之作,如《春秋》、《诗经》等,都无例外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才著文以舒其忿的。这样,就把忿和舒忿提到了一定的高度,忿成为一种崇高的情感,它不仅是不朽之作的基本动力,也是审美评价的主要标准,而具有高度发忿特点的《离骚》,自然也就成了“兼风雅之美”的作品之冠了。后来,韩愈也提出了“不平则鸣”的文艺观,继承了司马迁的文艺思想。这些文艺观大体亦被纳入儒家的范畴,对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我们可以从历代诸多古琴谱集中收有《离骚》、《广陵散》等舒忿乐曲这一点上清楚看到。从上可见“中和之音”有两个不同的侧面,一顺一逆均不失儒家道德规范,这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不可以静止的观点来对待它,应该从前期、中期、后期联系起来进行观察。

道家的“大音希声”主要核心应该是音乐在“道”不在声。而“道”须在清静无为之境方可悟得,故道家音乐观提倡一个“静”字。所谓“心静自然声希”,正说明了以意求声,强调了声对心的依赖和被动地位。另外,还否定了情感的抒发,心静自然无大幅度的情感可言,故其随心而生的声也就寥寥无几了。一切宜在玄想中解决问题,什么都不想,什么都解决了。在代表道家的音乐中,乐音的和缓运动只能被看作是心海微澜或心血来潮的似得“道”而未得“道”的表现,随之曲终声寂,则可入“道”之境矣!但这只是哲学上的道家音乐观,其结果势必导致陶渊明式的悬无弦琴于壁,这是为常人所不取的。而另一面却是道家的某些寓言故事为后世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不少的题材,音乐家们借用《庄周梦蝶》、《列子御风》这些故事中的游仙境界,来表达一种虚静、浪漫、自由的自我感受。让我们看《神奇秘谱》中明代臞仙为《庄周梦蝶》一曲所作的解题:
“臞仙曰。古有是曲。绝而无传者久矣。毛敏仲继之。庄子书日。庄周昔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不知周也。俄而觉则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蝴蝶之为周。周与蝴蝶必有分矣。此谓物化。是以达道之士。小造化于形骸之外。以神驭气。游燕于广漠之墟。与天地俱化。与太虚同体。斯乐非庸夫俗子之所能知也。达者得也。”
这段解题虽然体现了庄周齐物论的思想,但音乐是无法直接表现齐物论的,它给人的只是一种清静、虛淡的曲调用以表现飘忽的游仙感觉。因此,这类乐曲并不体现道家“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此等荒谬主张,而是在想象中所产生的某些心理、生理感觉的表述。
从以上儒、道两家的基本音乐观中,我们可以认为以屈原、司马迁、韩愈等为代表的直舒情性的美学观应是中国艺术史中的主流,它主张现实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它是向上的,这种主张在音乐史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广陵散》、《离骚》、《胡笳十八拍》、《潇湘水云》……不正是体现这种抒情论的典型作品么!前期儒家的“正统”中和思想提倡音乐的“逆欲法”,重视音乐陶冶情性的教化作用,这些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单一维护中庸的音乐观,对音乐的斗争性和娱乐性持否定态度,从而限制了音乐内容和形式的发展,这也是必须予以注意的。至于道家的“大音希声”,它比“中和之音”的“逆欲法”更限制了音乐形式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由于道家思想的附带物——浪漫主义的影响,给中国音乐中带来了一种游仙式的清新、恬淡风格,它以自由想象为特征,相比之下,可以使人从正统的中和之音的道学气味中得到一些调剂和解脱!这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有益于身、心的吧。

以上的音乐理想之实现途径又如何呢?古人认为大体当在个人的修养过程中来完成,而古琴正是他们的理想乐器。所谓“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不正是前期儒家“中和之音”的“逆欲法”概念么!而其目的为“导政事”的“舒怀论”及道家的“大音希声”也大体籍琴作为工具来实践他们的音乐理想的。这就强调了审美主体的自我完成过程,而这种自我完成过程正是为音乐创作中的情感生理直录法提供了产生和运用发展的基础条件。因为吾情吾自知,达其意而已矣的原则要求音乐情感形象的生理直录,而不要求过多地去阐发、论证、多侧面塑造……。那么,在交通不便的古代社会中,音乐如何才能起到应有的社会功效呢?古人云:“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之为琴。”这是说明功效由个别作用的积累而扩大到社会作用。这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故而有“士君子无故不撒琴瑟”、“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亲密,不离于身。非必陈设于宗庙乡党,非若锺鼓罗列于虚悬也。虽在穷阎陋巷、深山幽谷犹不失琴,以为琴之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喧哗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适足以和人意气,感人善心,故琴之为言禁也。”的说法和记载。


评论 0条评论
精彩评论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