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人必看的古今古琴第一美文,究竟写了什么?

《琴赋》是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嵇康创作的赋作,成书于魏晋玄学兴盛之际,融合其“声无哀乐”的美学主张与自然哲学思想。作品以琴为媒介,探讨音乐的本质与人格修养的关系。
全赋以琴材生长、斫制工艺、演奏境界为纲,描绘椅梧木生于崇山峻岭汲取天地灵气,经名匠雕琢为雅琴的过程。通过“崇山流波”“鸾凤和鸣”等譬喻刻画琴音变化,隐喻士人追求超脱尘世的精神自由。结尾“乱曰”部分强调雅琴唯至人能识,呼应“体清心远”的玄学特质,揭示音乐与人心相通但本质中和的观点。文中批判传统赋颂以悲为美的局限,主张琴德最优,构建乐器与人格境界的关联。尽管后世有关琴的文献众多,但精神的高度与审美的格调与此文相去甚远。
《琴赋》的艺术表达
《琴赋》长约2000字,赋的开头有序,赋尾有乱,是序乱兼备的赋体结构。嵇康在序中点明了抚琴的心志意趣,认为琴是乐器中最珍贵的,而“琴德最优”,琴乐的本质是“性洁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并对琴制、琴曲、典故、琴声、指法、乐理等特色进行了详论,虽是咏琴题材,却含有自喻的成分。咏乐器的赋作,汉代已有十数篇之多:枚乘的《笙赋》、王褒的《洞箫赋》、刘向的《雅琴赋》、刘玄的《簧赋》、傅毅的《舞赋》及《雅琴赋》、张衡的《舞赋》、马融的《长笛赋》、《琴赋》、侯瑾的《筝赋》、蔡爵的《琴赋》等。最早的完整乐器赋为王褒的(《洞箫赋》,稍后有马融的《长笛赋》,这两篇都是音乐赋的名篇,其源头可以上追到枚乘的《七发》中“首发”关于音乐之事的描写,“首发”短短200多字,无论是写桐树的生长环境、写制琴、写演奏还是写音乐之美,都极力通过遣词造句营造出一种趋于极致的艺术效果。《七发》不仅仅从创作程式上,同样也从其中所体现出来的音乐思想上,为后世的音乐赋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借鉴范本。嵇康《琴赋》却将前代咏物赋作了进一步发展:

第一,语言艳丽夸张,句式以骈散体为主。刘勰《文心雕龙·丽辞》言“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总观西晋辞赋,主导风格亦崇尚绮丽,与诗歌正相一致……而主要成就,亦在技巧、形式方面”。确实,比之前代的音乐赋,嵇康《琴赋》中骈俪句型已大量运用,更讲究词性联对的工整,对句的运用也比较普遍。“若乃重巘增起,偃蹇云覆,邀隆崇以极壮,崛巍巍而特秀;蒸灵液以播云,据神渊而吐溜。”这段文字描写了生长琴木的山川,四六言杂陈,展现了一种变化诡异的语言风格,突显出山峰所具有的险峻缥缈。
第二,用典精巧畅达,赋中用各种曲名连缀成句,化用曲名本身所代表的含义,使较呆板而互不关联的曲名在文中化为优美生动的意象。“下逮谣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别鹤,尤为一切,承间簉乏,亦有可观者焉。”蔡邕《琴操》曰,“昭君心念乡土,乃作怨旷之歌”。而《别鹤》崔豹《古今注》曰:“《别鹤操》,商陵牧子所作也。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母将为之改娶。妻闻之,中夜起,闻鹤声,倚户而悲。牧子闻之,呛然歌曰:将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远路漫漫。揽衣不寝食。后人因以为乐章也。”嵇康所陈列的这些郑卫之音,是根据他们相近的意象含义、典故出处,制造出怨妇游子的忧愁情调。

第三,营造优美形象的意境,表现抽象而无法具体把握的音乐,将模糊的音乐用清晰形象化的描写表达出来,并在赋作中灵活地用典故来烘托气氛。“纷淋浪以流离,负淫衍而优渥,璨奕奕而高逝,驰岌岌以相属,沛腾遌而竞趣,翕韡晔而繁缛。状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汤汤,郁兮峨峨。怫烦冤,纡余婆娑。陵纵播逸,霍濩纷葩。检容授节,应变合度。兢名擅业,安轨徐步。”高山之形,流水之声,被用来表现琴声流露的抑扬顿挫,以及音乐演奏中产生的不同风格,而这两个形象又出之有典。《吕氏春秋·本味》有“伯才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高山与流水代表的不仅仅是两种音乐风格,更是表现了弹琴之人迥然的气质秉性和人生追求。
《琴赋》的人生境界
《琴赋》超越前代作品并非只是在外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嵇康独抒心志,在赋作中表达了音乐人生的三种境界:
其一,贵在养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而弹琴则可以净化情欲,导养神气。琴不仅是士人身份的象征,也是士人相伴相依的佳侣,寄情托志的载体,更与士人构建出独特的心灵世界。嵇康生活在乱世之秋,满腔悲愤忧愁无从发泄,只好宣泄在琴声中。正如他所说:“处独穷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琴赋》)他的这种悲凉心绪,我们在与嵇康境遇相同的阮籍诗中也可以领略到,其《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在凄寒的月夜,清澈的月光照在帷帘上,孤鸿在野外啼叫,满腔的忧伤,溶入了这如泣如诉的琴声中,化进这清冷的月色里!古琴音色优美,韵致幽远而活泼,富于转折变化之妙,士人在风景优雅的竹林下,远离世俗的喧嚣,抚一首琴曲,沉浸在清峻幽深的琴韵中暂且忘怀政治的险恶多舛,排除宠辱得失,在老庄之道中逍遥,感受人生自由的乐趣。

其二,物我两忘。嵇康弹琴时,“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之十五》)的神妙意境一直为人所称颂。连晋朝大画家顾恺之都很想将之入画,却苦于无法下笔,而说“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以此可窥嵇康抚琴时,自然流露出超然放达、洒脱飘逸的境界。嵇康一生以老庄为师,处处追求老庄的超然放达、无欲无求的生命境界。《三国志·嵇康传》说嵇康曾“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乎千载之外者矣”。嵇康极其赞同古代圣贤、隐逸高人那种恬静无欲、寡淡自然的品格,以及他们游乎山泽、物我两忘的生活态度。在高轩飞观,广夏闲房之中,朗月垂空,秋风拂面之下,嵇康抚琴而歌:“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好仇,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琴赋》)这首有着浓厚老庄色彩的赋诗,很明显的表现了一种摆脱世俗、好仙向道、委身自然的生命境界。“瀛洲”,乃神仙所住之地;而“列子”,即庄周《逍遥游》中所说的“御风而行、汵然善也”神仙。“齐万物”乃是庄子重要的哲学理论,传达出泯火“物”“我”的对立,达到心志专一、虚静与“道”合一的思想。在幽远的琴声中,稽康忘掉生活中琐屑俗事,而进入自由境界,琴声、音韵与人心浑然为一,在艺术的王国里超度自我,到达与道合一的玄冥境界。
其三,独立精神。战国时代的庄子追求绝对的自由,他笔下扶摇千里的大鹏,御风而行的列御寇,以及藐姑射山上的神人等等,都可以达到一种不为外物所束缚、所统治的绝对自由的独立境界。而魏晋是一个士人心灵特别灵敏的时代,个体自由的时代,由儒而道释、由循名教而任自然及使老庄思想得到具体实现的时代。由于在政治上的实践难有建树,人们集中思考的不再是如何平治天下,而是更具超越性的世界之有无和在激荡的社会洪流面前生命的价值与人生态度。正如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魏晋士人摆脱了两汉陈腐经学的束缚,在文学、音乐、绘画等诸多艺术中,在山川大河、自然景物的反观中追求个人的精神解放,嵇康在“琴诗自乐”的音乐审美中,塑造独立的人格,培养自由的意志,达到“怡养悦愉,淑穆玄真,恬虚乐占,弃事遗身”(《琴赋》)的境界。个体生命的觉醒和艺术的独立带来了人与琴的天然契合,人之魅力与音乐之魔力如此地浑然一体,“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嵇康在他的《琴赋》中追寻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羁绊的精神世界,所演绎出人格的真性情、真道德、真精神,展示了艺术精神的真、善、美,以及所追求的自由意志。

《琴赋》展示了嵇康的艺术修养及高士襟怀,是音乐文学中的上乘之作,它在篇章结构、修辞及所包含的音乐思想方面都对后代音乐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就创作数量而言,汉赋中,咏音乐及乐器的作品只有10篇,到了魏晋就有25篇,后世咏乐器以及咏乐人、乐歌、乐曲的辞赋、诗、词、曲更不可胜数了。《琴赋》是嵇康音乐文学和美学思想形象化的体现,也是研究其音乐思想的重要文献。
文字来源:北京映雪山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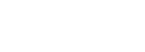
评论 0条评论
精彩评论
最新评论